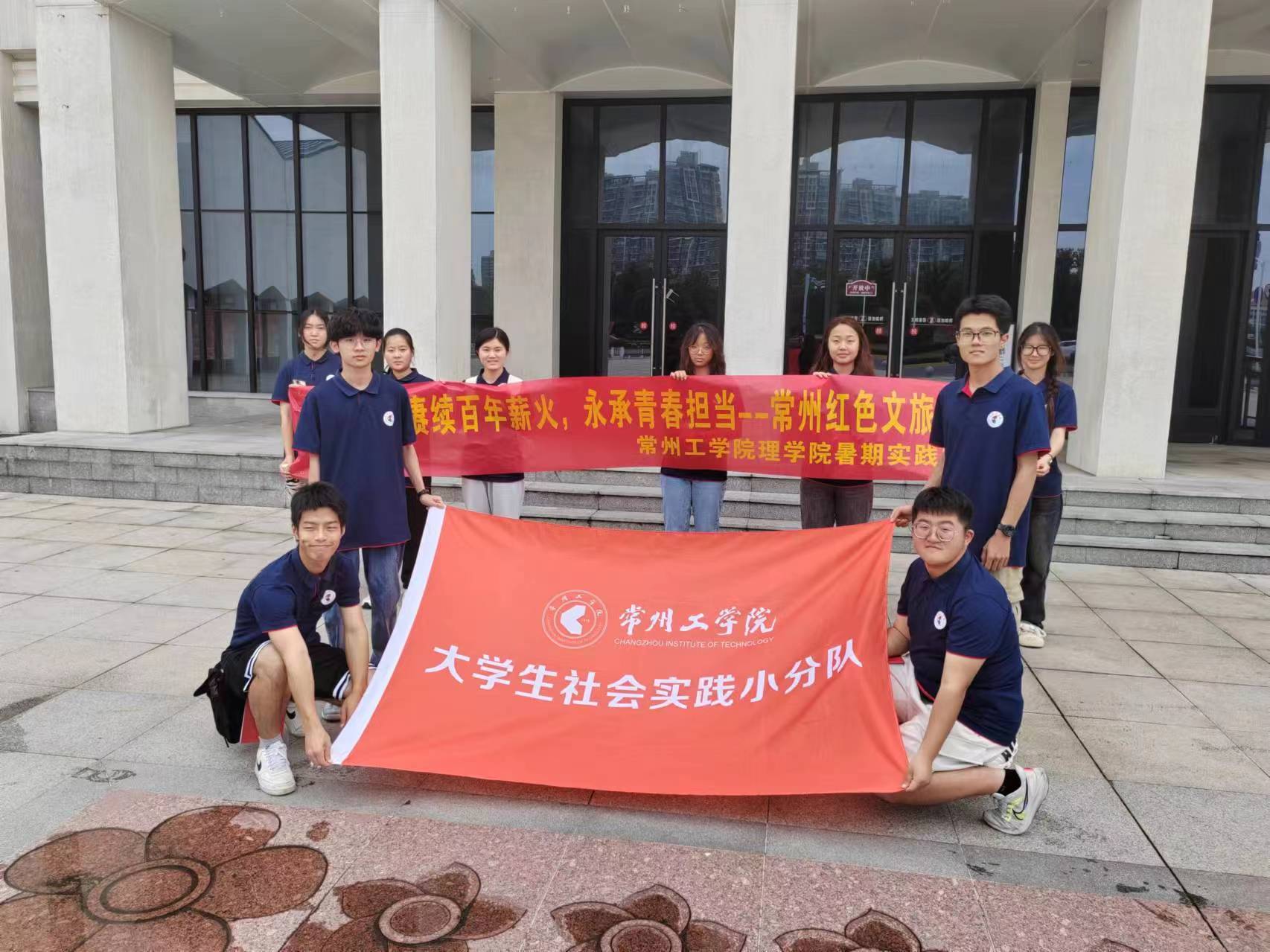多彩大学生网,大学生三下乡投稿平台
公民生态环境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2024年河海大学“追光”支教团社会实践
发布时间:2024-08-28 关注: 一键复制网址
摘 要
2024年7月,河海大学“追光”支教实践调研团在安徽省涡阳县圣尧小学支教期间,发现当地存在水华、垃圾乱扔等环境污染问题。为促进我国推动绿色发展,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不仅需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还需要民众的广泛参与。
本文基于2024年涡阳县部分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调查数据,通过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对我国公众私人领域环境行为和公共领域环保监督参与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环境态度和环境知识水平均与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环境行为呈正相关关系,但对政府环保工作力度评价和环境状况感知等外部因素对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环境行为的影响存在差异。公众对中央政府环保工作力度的评价均与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环境行为呈正相关,但公众对所在地政府环保工作力度评价与通过媒体和体制化渠道进行环保监督的行为呈负相关;感知到的当地环境问题影响严重程度对于私人领域环境行为的影响更大,对周边污染企业感知对于公共监督参与行为的影响更大。此外,在社会人口特征方面,年龄与公私领域环境行为均呈正相关关系,但性别、受教育程度、居住地类型对公私领域环境行为的影响方向存在差异。
关键词:环境行为;影响因素;环保公众参与;环境保护
目录
摘 要
第1章 绪论
1.1研究背景
1.2研究意义
1.3概念阐述
1.3.1环境保护
1.3.2环境行为
1.3.3环境公众参与
第2章 文献综述
2.1文献回顾
2.1.1国内文献回顾
2.1.2国外文献回顾
2.2研究综述
第3章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3.1理论基础
3.1.1“规范-激活”理论
3.1.2“价值-信念-规范”理论
3.2研究假设
3.2.1个体心理因素
3.2.2外部因素
3.3.3社会人口特征因素
第4章 研究设计
4.1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4.2变量设计
4.2.1被解释变量
4.2.2解释变量
4.2.3控制变量
4.3模型构建
第5章 实证分析
5.1描述性统计
5.2多重共线性检验
5.3回归结果分析
5.3.1环境态度与环境行为
5.3.2环境知识与环境行为
5.2.3环境状况感知与环境行为
5.2.4政府环保工作与环境行为
5.2.5社会人口特征变量与环境行为
第6章 结论与建议
6.1实证研究结论
6.2研究建议
参考文献
第1章 绪论
1.1研究背景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加速,以及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环境问题逐渐显现,如空气污染、水体污染、土地退化、生物多样性的丧失等,这些问题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了严重威胁。因此,绿色发展理念应运而生,强调的是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保护环境,实现经济、社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此外,绿色发展还与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密切相关。联合国制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旨在到2030年解决全球的贫困、不平等、气候变化、环境退化等问题,其中就包括了绿色发展的理念。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绿色发展理念的研究和实施变得尤为重要,包括但不限于绿色能源、绿色建筑、绿色交通、绿色金融等方面的研究和实践,都是为了实现绿色发展的目标。在这样的背景下,河海大学“追光”支教实践调研团在安徽省亳州市涡阳县圣尧小学支教过程中发现,虽然当地生态环境在近年来得到改善,但是当地居民生态环境保护意识薄弱、并且缺乏相关环保知识,据此,“追光”支教团为传播生态环保知识设计了问卷并在当地展开调研。
1.2研究意义
生态环境保护关乎地球的生态平衡、人类的健康福祉以及可持续发展的未来。通过推广绿色生活方式和环保技术,我们能够减少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与污染,有效应对气候变化、空气污染、水资源短缺等全球性环境问题。生态环境保护的意义在于促进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和谐共生。它鼓励人们采用低碳、节能、可循环的生产和消费方式,不仅推动了绿色经济的崛起,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和经济增长点。同时,绿色环保行动也是提升公众环境意识、培养责任感的重要途径,促进了社会文明的进步,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1.3概念阐述
1.3.1环境保护
环境保护,指的是人类为解决现实或潜在的环境问题,协调人类与环境的关系,保障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而采取的各种行动的总称。其涵盖了众多方面,包括但不限于对自然环境(如大气、水、土壤、生物等)的保护,防止污染和破坏;对生态系统的维护,促进生态平衡;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以确保资源的可持续性;以及通过教育、法律、政策等手段,提高公众的环境意识和推动全社会共同参与环境保护行动。环境保护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创造一个清洁、健康、美丽且适宜人类居住和发展的环境。
1.3.2环境行为
环境行为是指个体或群体与周围环境相互作用的各种表现和活动。它包括人们在日常生活、工作、学习和休闲等各种情境中,对环境的感知、认知、态度和行动。比如个人选择绿色出行方式、节约能源、垃圾分类等,企业采取环保生产措施、减少污染物排放等,以及社区组织开展的环保活动等都属于环境行为。环境行为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个人的价值观、知识水平、经济状况、社会文化背景,以及环境政策、信息传播等外部因素。对环境行为的研究有助于深入了解人类活动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从而制定更有效的环境保护策略和促进可持续发展。
1.3.3环境公众参与
环境公众参与,指的是社会公众在环境保护领域中,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自愿、平等地参与环境决策、环境管理、环境监督以及环境教育等相关活动的过程。其核心在于保障公众对环境事务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使公众能够有效地介入环境保护工作,促进环境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和透明化。公众可以通过参与环保组织、社区活动、公众听证会、提供意见建议、监督企业环境行为等多种形式,为环境保护贡献力量。环境公众参与有助于增强公众的环境意识,推动环境保护工作的有效开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以及可持续发展。
第2章 文献综述
2.1文献回顾
2.1.1国内文献回顾
国内环境行为研究起步较晚。在早期研究中,不同学者对于环境行为阐释不同。有学者从社会学的角度阐释环境行为,认为“环境行为是与特定社会的各种因素相关,以一定的社会关系形式进行并且其结果不仅会对环境产生影响,而且会影响到其他的社会关系的一种社会行为”(崔凤、唐国建,2010)[1]。有学者立足西方环境行为理论,认为“环境行为是采取有助于改善、增进或维持环境品质的行动。在生活中身体力行,以达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目的”(孙岩,2006)[2]。也有学者从环境行为与环境意识关系的角度出发,将环境行为从环境意识中进行了剥离,使环境行为成为后来专门而深入的研究方向(王玲,2011)[3]。目前我国环境行为内涵主要概括为广义和狭义。广义的环境行为不仅包括保护行为,也包括破坏行为,狭义的环境行为主要指环境保护行为(王晓楠,2019)[4]。本文研究的环境行为从狭义出发,即“个体在日常生活中主动采取的、有助于环境状况改善与环境质量提升的行为”(彭远春,2011)[5]。
学界对环境行为影响因素的解释众多,主要包括个体心理因素、社会人口特征因素和外部因素(贾如、郭红燕、李晓,2020)[6]。个体心理因素方面,公众个体所拥有的环境知识、环境治理技能、环境治理资源和身体素质等条件在参与环境治理行为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刘静静,2023)[7]。数字素养(刘长进、王俊雅等,2023)[8]、个人导向心理所有权与集体导向心理所有权(张琳琳,2023)[9]、自然共情、敬畏、环境价值观(龙燕棱、周永红,2023)[10]等也会公民环境行为有显著促进作用。社会人口特征因素方面,社会网络和社会规范对个体环境行为具有直接影响,社会信任和社会规范对团体环境行为具有直接影响(杨金梅,2024)[11]。社会交往、社会信任也均在环境行为中发挥积极作用(张莉琴、方醒等,2024)[12]。也有学者在研究社会阶层对环境行为的影响中提出,社会阶层对个人亲环境行为的影响差异:来自中层家庭的个人的亲环境行为最强;社会阶层对女性亲环境行为的影响程度高于男性;社会阶层对农村居民亲环境行为的影响程度高于城镇居民(王敏、王峰,2023)[13]。外部因素中,有学者认为当前我国在环境治理方面存在公众参与路径较少、参与途径不畅通等问题,政府对公众这一主体在环境治理当中发挥的作用不够重视(张成博,2021)[14]。同时,时间能力认知、信息畅通程度、设施便利程度、政策补贴情况也能在农户参与环境整治中起到正向的影响作用(张海鹏,2024)[15]。
2.1.2国外文献回顾
国外关于环境行为的研究早于国内(吴桂英,2014)[16]。国外对环境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可以从心理性因素以及内外因素结合两个方面梳理 (彭远春,2013)[17]。侧重心理性影响因素的研究模式方面,诸多学者直接利用计划行为理论对环境行为进行了研究,其中有学者提出:单独对感知到的行为控制加以考察时,其对环境行为有着显著作用;但将其与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综合考察时,感知到的行为控制对环境行为的作用无足轻重(KAISER F G、GUTSCHER H,2003)[18]。也有学者探讨了环境素养模式中相应变量对负责任环境行为的贡献力。结果显示,环境敏感度、环境行为策略知识与技能、个体控制观、群体控制观、对待污染与技术的态度、心理性别角色等影响环境行为,其中环境敏感度、环境行为策略知识与技能对环境行为最具影响力(Sia A P、Hungerford H R、Tomera A N等,1986)[19]。在借鉴计划行为理论以及参照环境素养模式的基础上,有学者提出一个负责任的环境行为模式,即除环境议题知识、行为策略知识、行为技能、态度、控制观、个人责任感以及行为意向与负责任的环境行为有关外,还存在影响环境行为的情境因素,如经济条件、社会压力、从事环境行为的机会等(Hines J M、Hungerford H R、Tomera A N,1987)[20]。内外因素结合的综合性研究方面,有学者提出预测环境行为的A-B-C模型。该模型将内在心理过程与外在条件加以整合,认为环境行为(Behavior)是个体一般与具体的环境态度(Attitude) 和社会结构、社会制度与经济动力等外在条件(External Conditions) 共同作用的结果(Guagnano G A、Stern P C、Dietz T,1995)[21]。而有的学者对环境主义的探讨则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侧重探讨社会人口特征与环境主义的关系; 二是着重探讨价值观、信念、世界观以及其他社会心理变量与环境主义的关系(Dietz T、Stern P C、Guagnano G A,1998)[22]。但是,也有其他学者指绝大多数环境行为模式具有局限的原因在于,其对个体、社会以及制度约束缺乏考虑,且往往假定人是理性的,能系统获取和利用各种信息。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其认为环境关心与亲环境行为之间存在个性、责任与可行性三个方面的阻碍。同时,其进一步指出日常生活领域的环境行为与不同的情境有关,最为一般的是社会结构与文化背景,如工业化程度、富裕水平、社会分化与整合的形式等,进而对行动者的生活以及体验现实的方式产生影响(Blake J,1999)[23]。
2.2研究综述
总体而言,对于公民生态环境行为的影响因素,无论是定性研究还是定量研究,国内外学者都有不同的观点。但学术界普遍认为,个体因素、社会因素和外部因素都会对公民环境行为产生影响。国内外文献中针对个别影响因素的分析较多,但是对影响因素综合性、全面性的研究较少。
第3章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3.1理论基础
3.1.1“规范-激活”理论
“规范-激活”理论认为个体规范是影响利他行为最直接的因素, 而个体规范受结果意识和责任归属的影响。
“规范-激活”理论主要由三个变量构成,分别是结果意识(awareness of consequence)、责任归属(ascription of responsibility)、个体规范(personal norms)。
“结果意识”是指个体对因为未实行利他行为而给他人或者其他事物造成不良后果的意识。通常情况下,个体对于在一定情况产生不良后果的感知越强烈,道德义务感则越强,个体则越可能激活个体规范去实行相应的利他行为。
“责任归属”是指个体对于不良后果的责任感。个体对于结果的责任感越强,就越有利于实行与个体规范相符的行为。
“个体规范”是指个体在一定情况下实行具体行为的自我期望。个体规范是被内化的社会规范,是自我的道德义务感。违反个体规范时,个体会产生罪恶感、自尊的丢失或者自我否定;反之,遵守个体规范时,个体会产生自豪感以及自尊的提升。
“规范-激活”理论自提出30多年来,已经被广泛地应用于研究西方发达国家的亲社会行为包括环保行为,并且被证明了该理论具有良好的预测力和解释力(张晓杰、靳慧蓉、娄成武,2016)[24]。
3.1.2“价值-信念-规范”理论
“价值-信念-规范”理论在“规范-激活”理论的基础上增加了“价值”、“新环境范式”两个主要变量。
1.价值
不同的价值取向会直接影响主体与其价值取向一致的环境保护意愿。通常,价值取向被区分为以下三类:
(1)利己价值取向:社会行为主体在实行环保行为时,将试图最大化个体利益,并且往往追求最大化自身经济利益。
(2)利他价值取向:社会行为主体在实行环保行为时,将注意到其他人类群体的福利,努力最大化社会群体利益,然而但这类人常常忽视非人类物种的福祉。
(3)利生物圈价值取向:社会行为主体在实行环保行为时,将不仅考虑到人类群体的福利,同时也会关注非人类物种的利益
通常来说,主体的价值取向对其行为没有较强的直接影响,二者间的关系通常还由其他因素所介导。因此价值变量成为“价值-信念-规范”理论模型因果链中最基础的研究变量。
2.新环境范式
新环境范式非常强调环境因素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和制约,认为人类的行为已经对脆弱的生态环境造成持续的不良影响。Dunlap等人(2000)[25]认为,认同新环境范式的人越多,环境状况改善的前景就越有希望。
“价值-信念-规范”理论认为价值取向、新环境范式、结果意识、责任归属和个体规范五个变量构成密不可分的因果链。在该因果链模式下,公众环保行为由个体规范所激活,个体规范由个体对因为未实行利他行为而给他人或者其他事物造成不良后果的意识(即结果意识)和个体对于不良后果的责任感(即责任归属)所激发,结果意识和责任归属本身则受到个体的价值取向和环境关心影响。
“价值-信念-规范”理论是“规范-激活”理论在环保行为研究中的拓展,在公众环保行为研究方面比“规范-激活”理论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张晓杰、胡侠义、王智奇,2017)[26]
3.2研究假设
3.2.1个体心理因素
随着心理学行为理论的兴起,早期环境行为研究汲取了心理学中的计划行为理论、“规范-激活”理论以及“价值-信念-规范”理论等,从而构建了环境行为领域的“态度-行为”研究框架。该框架认为,在特定情境下,个体的环境行为主要由其行动意愿所决定。“价值-信念-规范”理论认为,个人具有与环境状况关联的价值观,当个人意识到不采取某种行动会对环境带来负面影响而危及自己的价值,同时为自己有能力采取行动去减免环境威胁时,则感觉到有义务采取对环境有利的行动,就可能采取环保行为。因此个人环境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价值观、环境观、对自身行为潜在环境危害的认识、对自身行为能够减少环境危害的信心,以及由此产生的环境责任感。
Hungerford(1990)[27]从环境教育学的角度拓展了“态度-行为”框架,提出“知识-态度-行为”理论,认为环境知识能够通过态度影响行为。大部分实证研究承认环境知识对环境行为的重要作用。彭远春(2015)[28]根据CGSS2003和CGSS2010调查数据对环境认知水平和环境行为进行了探讨,发现环保知识、公众对环境污染危害程度的环境风险认知和环境问题严重性认知均对环境行为有显著影响。
基于以上文献提出研究假设:
H1:环境态度与涡阳县公民私人领域环境行为呈正相关关系。
H2:环境态度与涡阳县公民公共领域环保监督参与行为呈正相关关系。
H3:环境知识水平与涡阳县公民私人领域环境行为呈正相关关系。
H4:环境知识水平与涡阳县公民公共领域环保监督参与行为呈正相关关系。
3.2.2外部因素
随着研究的深入,国内外研究者越来越关注到,环境污染状况、政府环境治理行为、社会规范、等外部因素对公民环境行为的影响。
在外部因素研究中,环境质量状况和政府环境治理水平被视为最重要的两个影响因素。“污染驱动假说”认为,如果周围污染问题变得严重,公众会为维护自身环境权益而改善环境行动。同时,由于我国政府在环境治理中占据主导地位,对生态环境状况有着重要影响,也对公众行为有着引导和示范作用,因此国内学者将政府环境治理情况也视为重要的外部影响因素。
基于以上文献提出研究假设:
H5:涡阳县公民对当地环境污染状况的感知与其私人领域环境行为呈正相关关系。
H6:涡阳县公民对居住地周边污染企业的感知与其公共领域环保监督参与行为呈正相关关系。
H7:涡阳县公民所在地政府环保工作水平与涡阳县公民私人领域环境行为呈正相关关系。
H8:涡阳县公民所在地政府环保工作水平与涡阳县公民公共领域环境行为呈正相关关系。
H9:中央政府环保工作水平与涡阳县公民私人领域环境行为呈
正相关关系。
H10:中央政府环保工作水平与涡阳县公民公共领域环境行为呈正相关关系。
3.3.3社会人口特征因素
研究表明,社会人口特征因素如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和居住地等也会对环保行为产生显著影响。在年龄方面,有国内研究显示,中青年、中年、中老年会在私人环境领域表现得更好。在受教育程度方面,多数研究者承认受教育程度对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环境行为的促进作用。在居住地方面,大部分研究表明,我国居民环境行为存在显著的城乡差距和社会阶层差异,城镇居民、社会阶层较高居民的环境关注度更高。
但现有研究关于性别和收入的影响仍存在争议。在性别方面,大部分研究认为女性比男性环境行为表现更好。我国学者龚文娟(2007)[29]通过对200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发现女性比男性更加倾向于采取私人领域的环境友好行为。但也有研究表明,性别假设不一定适用于所有环境行为领域,如由于家庭分工不同,男性可能更多地采取家庭资源回收行为,且由于传统上男性更多地参与社会事务和政治活动,所以可能比女性更多地参与公共环保事务。
在收入水平方面,有观点认为高收入群体一般对环境问题更为敏感,如钟念(2018)[30]等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0年数据发现,公众收入水平与其环境关心和环境友好行为呈显著正相关。但也有相反的观点认为,低收入群体由于生活环境状况较差,从而更加关注环境问题,而社会经济状况较好的公众则关注较少。也有其他研究表明,收入对环境行为的影响并不显著,高收入群体与低收入群体的环境行为差距不大,因此收入因素对于公众环境参与行为的影响有待进一步研究。
第4章 研究设计
4.1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样本选取旨在全面且准确地反映研究主题所涉及的对象。总体范围界定为安徽省亳州市涡阳县,选择该总体是因为其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依据年龄将总体分为不同层次,以确保样本在各个层次上的分布均衡。样本规模确定为224人,此规模基于预先设定的统计功效分析和研究资源的实际情况。数据来源主要包括一手的问卷调查和二手的官方统计数据。问卷调查于7月22日至7月26日期间在安徽省亳州市涡阳县双庙镇进行,共设计了19个问题,涵盖了环境污染的种类、环境污染是否得到改善、居民在改善环境行动中的参与度等方面。在问卷发放和回收过程中,严格遵循调查规范,有效回收率为98%。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了数据清洗,剔除了无效和缺失值,随后采用SPSS 27软件对经验数据进行处理分析。然而,由于时间和资源的限制,样本规模可能相对较小,可能无法完全涵盖总体的所有特征。在后续的分析和结论中,将充分考虑这些局限性。
4.2变量设计
4.2.1被解释变量
鉴于公众在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环境行为存在较大差异,本研究将“私人领域环境行为”和“公共领域环保监督参与行为”作为主要因变量,全面考察其影响因素并比较影响因素的异同。
为得到私人领域环境行为变量,首先将公众在10个方面的环境行表现得分(1~5分)经过同向化处理后进行加总平均,并为了方便与公众的监督参与行为变量进行对比,根据平均分是否在4分及以上处理为二分变量,其中4分及以上意味着公众整体上“总是”或“经常”践行各类环境行为。同时,为了弥补多数研究将私人领域环境行为作为单一整体变量进行研究、无法比较不同类型行为差异的问题,本文选取“随手关灯、及时关闭电器电源”等节电行为和“选购绿色产品和耐用品、不买一次性用品和过度包装商品”绿色消费行为作为私人领域具体环境行为的因变量,其中前者代表着减少生活成本的环境行为,而后者代表着可能提高消费支出的环境行为。
公共领域环保监督参与行为变量为二分变量,来自于本次受访者对过去三年中是否针对企业环境污染问题采取过行动的调查,采取行动的渠道包括“直接找企业协商”“向当地政府相关部门反映污染问题”“向当地街道、居委会或村委会反映情况”“通过上访向上级政府反映污染问题”“向媒体反映情况,引起舆论关注”“寻求民间环保团体的帮助”和“把事情直接曝光到网上”。同时,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受访者使用不同监督渠道的比例差异较大,在过去三年中采取过监督行动的人群中,使用地方体制化渠道的比例最高,“向当地街道、居委会或村委会反映情况”占37.5%,“向当地政府部门投诉举报”占25.8%;其次是媒体渠道,选择“向媒体反映情况,引起舆论关注”占17.9%。因此选取“是否通过媒体渠道监督参与”和“是否通过地方体制化渠道监督参与”作为公共领域具体监督参与行为的因变量。
表1 被解释变量相关变量测量
4.2.2解释变量
环境态度:包括私人领域环境行为重要性和公众监督参与行为重要性,其中私人领域环境行为重要性变量,由受访者对十类环境行为对于保护我国生态环境的重要程度打分(1~5分),再进行加总平均得到,公众监督参与行为重要性变量由受访者对六类环保监督参与行为对于促进企业环境保护的重要程度打分(1~5分),再进行加总平均得到。
环境知识:环境知识指公众对于环境问题、环境科学技术和环境治理的一般性认知状况(洪大用,范叶超,2016)[31]本研究中由4道环保知识判断题回答正确数量进行测量,题目涉及“公民十条发布情况”“露天烧烤会产生PM2.5”,“雾霾的产生与散煤燃烧是否有关”和“全国统一环保举报热线电话是12369”,基于样本量考虑,将回答“不知道”的纳入错误选项。
环境状况感知:由受访者对当地环境状况的评价得出,包含“是否认为居住地周边有污染企业”和“认为当地环境问题对自身影响程度”两个题项。环境状况感知变量受到宏观的地方环境质量影响,但又更为具体地反映了公众对居住地周边环境的不同感受。外在的地方环境质量只有被公众内化为对环境质量的认知,才会进一步影响环境行为,因此用公众的个体环境状况感知变量替代宏观的地区环境质量变量。
政府环保工作:考虑到中国政府在环境治理领域的突出影响,在模型中纳入“政府环保工作状况”变量,由“对所在地政府环保工作力度评价”和“对中央政府环保工作力度评价”两个题项进行测量,赋值分别为0~10分。
4.2.3控制变量
根据既有研究,选取性别、年龄、居住地、受教育程度、工作单位性质和家庭税后年收入作为控制变量。综上所述,本研究所使用的变量描述见表2。
表2 变量定义表
4.3模型构建
本文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将考虑环境态度、环境知识水平、环境状况感知等因素对公众私人领域环境行为的影响来分析十个研究假设。为验证
假设H1:环境态度与私人领域环境行为呈正相关关系。
假设H2:环境态度与公共领域环境行为呈正相关关系。
假设H3:环境知识与私人领域环境行为呈正相关关系。
假设H4:环境知识与公共领域环境行为呈正相关关系。
假设H5:当地环境污染状况感知与私人领域环境行为呈正相关关系。
假设H6:当地环境污染状况感知与公共领域环境行为呈正相关关系。
假设H7:所在地政府环保工作水平与私人领域环境行为呈正相关关系。
假设H8:所在地政府环保工作水平与公共领域环境行为呈正相关关系。
假设H9:中央政府环保工作水平与私人领域环境行为呈正相关关系。
假设H10:中央政府环保工作水平与公共领域环境行为呈正相关关系。
构建两个Logistic回归模型:
模型1:分析私人领域环境行为(Y1)
Logit(P(Y1=1))=β0+β1A+β2K+β3E+β4L+β5C+β6Age+β7G+β8Education+β9Residence
模型2:分析公共领域环境行为(Y2)
Logit(P(Y2=1))=β0+β1A+β2K+β3E+β4L+β5C+β6Age+β7G+β8Education+β9Residence
其中,β为回归系数,Y1为私人领域环境行为,Y2为公共领域环境行为,A为环境态度,K为环境知识,E为环境状况感知,L为地方政府环保工作评价,C为中央政府环保工作评价,Age为年龄,G为性别,Education为受教育程度,Residence为居住地类型。
通过回归分析得到每个自变量的回归系数(β),可以判断各因素对环境行为的影响方向和显著性。
第5章 实证分析
5.1描述性统计
私人领域环境行为均值为0.2795,标准差为0.449,表明公众的节电以及绿色消费行为在日常生活之中较少做到;公众领域监督参与行为均值为0.6343,标准差0.482,表明该地区公众有一定的监督意识,但参与程度高低不平。综合各项数据表明本研究有进行的意义与可能。
表3 公众环境行为变量描述性统计
注:样本量为224。
5.2多重共线性检验
本研究运用SPSS27分析软件对公众私人领域环境行为和公共领域监督参与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在回归分析前,对模型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表明各模型的VIF值均大于1且小于3,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5.3回归结果分析
表4 公众环境行为相关变量回归分析结果
注:*p<0.1,**p<0.05,***p<0.01。
5.3.1环境态度与环境行为
由回归分析结果可知,环境态度与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环境行为均成正相关关系。考虑到控制变量,公众认为私人领域环境行为对于保护我国生态环境的重要性每提高一个等级,其积极采取私人领域环境行为的概率比原来提升26%,积极节电和选购绿色产品的概率比原来分别提升10%和13%。同时,公众认为公共监督参与对于促进企业环境保护的重要性每提升一个等级,其针对企业环境污染问题采取过监督行为的概率比原来提升38%,通过媒体渠道和地方体制化渠道监督的概率均比原来提升34%。由此可以验证假设1和假设2,在“价值-信念-规范”理论的作用下,若公众认为自身的环境行为越重要,就会更加积极的采取行动。
5.3.2环境知识与环境行为
根据回归结果,环境知识水平与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环境行为均呈正相关关系,且对公共监督参与行为有较大影响。四道环境知识判断题中,公众每多答对一道题,则私人领域环境行为表现较好的可能性将是原来的2.69倍,“总是”或“经常”节电和选购绿色产品的可能性分别是原来的2.04倍和2.46倍,采取过监督参与行为的可能性将是原来的3.62倍,通过媒体渠道监督和通过地方体制化渠道监督的可能性分别是原来的2.89倍和4.21倍。综上,可以验证假设3和假设4,证明了环境知识对公、私领域环境行为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5.2.3环境状况感知与环境行为
模型一、二、三显示,环境状况感知对私人环境行为有显著影响。在控制变量的条件下系统地改变影响因素,受访者认为当地环境问题对其自身影响的严重程度与私人领域行为、节电行为和绿色消费行为均呈正相关关系。同时还认为当地环境问题的影响程度每严重一个单位,认为私人领域环境行为受影响的可能性比原来提升37%;主动节电的可能性较原来提升13%;积极进行绿色消费的可能性比原来提升22%。
由模型四、五、六可知,环境状况感知与监督参与总体行为无显著相关性,但对通过媒体渠道监督和通过地方体制化渠道监督均呈正相关关系。在控制变量的条件下,受访者认为居住地周边存在污染状况进尔通过媒体渠道监督的可能性提升38%,通过地方体制化渠道监督的可能性提升43%,说明受访者所代表的公众群体对居住地周边污染源反应程度较对私人领域环境行为污染的感知程度更强,同时采取措施维护自身权益的概率也更高。
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公众居住地附近污染源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一旦公众感知到生活环境周边存在污染状况,出于自身环境安全权益考虑,就会更迫切地想要通过专业的方式对污染源采取措施,同时自家附近的污染源相较于较远的污染源而言更可能激发公众监督参与的责任感和行动力。同时,公众认为当地环境问题的影响严重程度每上升一个单位,则通过媒体渠道监督和通过地方体制化渠道监督的概率比原来分别提升24%和20%。这基本验证了假设5和6的“环境污染驱动论”。
5.2.4政府环保工作与环境行为
公众对中央和所在地政府环保工作力度评价对其公共与私人领域环境行为均有显著影响,但在影响方向上有一定差异。对中央政府环保工作力度评价的影响程度相对较大。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公众对中央政府环保工作力度评价与公共和私人领域环境行为均呈正相关关系,且对节电行为、绿色消费行为、通过媒体渠道监督和通过地方体制化渠道监督均有一定正面影响。这可能是由于全国环保工作力度的加强对公众环保行为有潜移默化的表率作用,有助于提升公众的环境意识和责任感,从而积极践行各类环保行为。以上结果验证了假设7和假设8。但是,与假设九和假设十不相符合的是,公众对所在地政府环保工作力度评价对公共和私人领域总体环境行为均无显著影响,并且与通过媒体渠道和地方体制化渠道监督呈负相关关系,尤其是对通过媒体渠道监督的负向影响相对较大。这可能是因为地方政府环保工作力度与当地环境质量关系更密切,因此公众认为如果当地政府有能力保护好环境,就降低了监督参与的紧迫感,即便要监督参与,也更倾向于选择地方体制化渠道而不是媒体渠道;相反,如果公众认为所在地政府环境管理工作不利,那么公众将更加迫切地使用自身的监督权。
5.2.5社会人口特征变量与环境行为
社会人口特征变量中,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和居住地类型对公共与私人领域环境行为均有显著影响。
第一,性别对公共与私人领域环境行为的影响不同,女性更偏向于采取私人领域环境行为,而男性则更倾向于通过媒体渠道和体制化监督参与环保。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男性私人领域环境行为表现整体较好的概率仅为女性的二分之一不到,积极节电和选购绿色商品的概率也仅为女性的0.87倍和0.92倍,但男性通过媒体渠道和体制化监督的概率是女性的1.84倍和1.14倍。
第二,年龄与公共与私人领域环境行为均呈正相关,且年龄对私人领域环境行为影响较对公共领域环境影响大。40岁以上的群体更倾向于采取私人领域环境行为,而60岁及以上人群私人领域环境行为表现较好的概率是25岁及以下人群的近4倍,节电和绿色消费行为也呈现出一致的趋势。25岁以上人群在公共监督参与领域的表现均好于25岁及以下青年群体,60岁及以上人群总体监督参与行为表现相对最好,但相比私人领域环境行为增幅较小,且根据显著度和系数可知,年龄对通过体制化监督的正向作用比通过媒体渠道监督更大。
第三,受教育程度对公共与私人领域环境行为的影响不同。一方面,高学历人群的私人领域环境行为比低学历人群表现相对较好,在节约用电方面也更为积极;另一方面,高学历人群监督参与行为总体相对较少,但更多地通过媒体渠道监督,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高学历人群更善于使用媒体资源表达自身诉求。此外,受教育程度对公众购买绿色产品等色消费行为和通过体制化监督无显著影响。
此外,家庭年收入与私人领域环境行为总体不显著相关,但与节电行为和绿色消费行为均显著相关,且呈反向关系。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家庭年收入10万元及以上的家庭更倾向于随手关灯、及时关闭电器的概率是收入较低家庭的0.82倍,但在购买绿色产品和耐用品等绿色消费方面,能够做到的概率是收入较低家庭的1.13倍。这意味着,各类私人领域环境行为存在较强的异质性,在研究收入水平和便利性等因素时不能只考虑对总体环境水平的影响,还要考虑对不同类型行为的影响差异。
第6章 结论与建议
6.1实证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2024年涡阳县部分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调查数据,对我国公众私人领域环境行为和公共领域监督参与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对比研究,通过影响因素模型搭建与回归分析,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1)环境态度与环境知识与公私领域环境行为成正相关关系。环境态度会引导环境行为,而当大众的环境知识水平越高,公民更愿意采取环境友好行为。其主要机制是,大众通过环境知识的学习,把正确的环境态度和制度规范转变为自己的价值观,潜移默化于生活中,从而约束自己的行为。其中,环境知识水平对公共监督参与行为的影响相对较大。
(2)环境状况感知能够影响公私领域环境行为,但影响程度存在差异。环境状况感知中当地环境问题对私人领域环境行为存在显著影响;居住周边存在污染企业对其几乎没有影响。其中,对周边污染企业的感知对公共监督参与行为的影响更大,感知到周边存在污染企业,公众更愿意通过媒体渠道或地方体制化渠道采取监督行动。
(3)公众对中央和所在地政府环保工作力度评价对其环境行为的影响存在差异,公众对中央政府环保工作力度评价的影响相对较大,且呈正相关;对所在地政府环保工作力度评价与公私领域整体环境行为不显著相关。其中,经济奖励类政策对居民的环境行为影响显著,命令式对公众环境行为无明显影响。
(4)不同的公民禀赋对生态环境行为的影响存在差异。年龄对环境行为影响呈正相关关系。性别、受教育程度、居住地对公私环境行为影响差异化,女性更愿意主动以个人行为去保护生态环境,而男性更积极地参与环境法规与环境监督活动;高学历者相对于低学历人群存在更多的环境友好行为,且更多地进行环境法规的了解与环保状况的监督;城市居民较农村居民的私人领域环保行为表现较好,但总体上也缺乏对环保的监督活动。
(5)家庭收入水平对与具体的环境行为有一定影响,与降低生活成本的节电行为呈负相关,但与可能提高消费支出的绿色消费行为呈正相关。
6.2研究建议
根据此次调研实证研究得出的,对公私领域生态环保行为的积极正相关关系,本文得出以下启示:
(1)加强生态知识的宣传教育,提高公民的生态知识认知。借助电视、网络等传播媒介让生态意识深入人心,推动公民转变传统行为,引导树立以“生态利益”为中心的价值观。同时,可以进行社区环保大讲堂,科普系列活动,帮助培养公民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让居民自觉保护周边生活环境,将保护生态环境作为一种自觉的行为。
(2)有效化规范公民环保行为,多途径帮助环保政策落实落地。首先,要从多方面多种形式来推动居民知法、守法、用法,增强对环保法律制度的认识,使环保法制观念深入人心,进而增强公民的生态法制意识。但更要注意的是通过秸秆还田补贴、农业补贴、技术下乡等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举措对公民进行激励与引导。
(3)降低实施生态行为的障碍,提高公民对居住地附近环境状况感知和控制能力。要采取多种方式来减少居民在实施生态行为中所遇到的困难。首先,增加社会教育培训。如垃圾分类等。其次,增添多类垃圾桶、旧衣回收设施,绿色产品等环保基础设施和环保用品,为公民提供进行环保行为的多样化途径,方便进行生态友好行为。
参考文献
[1]崔凤, 唐国建. 环境社会学:关于环境行为的社会学阐释 [J]. 社会科学辑刊, 2010, 03): 45-50.
[2]孙岩. 居民环境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D], 2006.
[3]王玲. 国内环境行为研究综述 [J]. 农村经济与科技, 2011, 22(08): 15-7.
[4]王晓楠. 我国环境行为研究20年:历程与展望——基于CNKI期刊文献的可视化分析 [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19, 33(02): 22-31.
[5]彭远春. 试论我国公众环境行为及其培育 [J].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 11(05): 47-52.
[6]贾如, 郭红燕, 李晓. 我国公众环境行为影响因素实证研究——基于2019年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调查数据 [J]. 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2020, 45(01): 56-63.
[7]刘静静. 公众参与城市环境治理行为影响因素研究 [D], 2023.
[8]刘长进, 王俊雅, 李宁, 滕玉华. 数字素养对农村居民“公”领域亲环境行为的影响研究 [J].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3, 23(04): 12-20+83.
[9]张琳琳. “我的”还是“我们的”:心理所有权对亲环境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 [D], 2023.
[10]龙燕棱, 周永红. 自然共情与亲环境行为的关系:一个链式中介模型 [J]. 心理月刊, 2023, 18(20): 27-30.
[11]杨金梅. 社会资本对环境行为的影响机理研究 [J]. 当代经济管理, 2024, 46(08): 47-52.
[12]张莉琴, 方醒, 陈定倩. 社会交往对亲环境行为的影响:社会信任与环境关心的中介作用 [J]. 兵团教育学院学报, 2024, 34(04): 25-31.
[13]王敏, 王峰. 社会阶层、环保认知与亲环境行为——基于环境社会学视角的实证研究 [J]. 复旦公共行政评论, 2023, 02): 252-76.
[14]张成博. 基于TPB-VBN整合模型的公众参与环境治理行为影响因素研究 [D], 2021.
[15]张海鹏.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中农户参与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 [D], 2024.
[16]吴桂英. 国内环境行为研究综述 [J]. 经济研究导刊, 2014, 14): 7-9.
[17]彭远春.国外环境行为影响因素研究述评[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23(08):140-145.
[18]KAISER F G, GUTSCHER H. The Proposition of a General Version of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Predicting Ecological Behavior [J].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2003, 33(3): 586-603.
[19]Sia A P,Hungerford H R,Tomera A N,et al. Selected Predictors of Responsible Environmental Behavior: An Analysis[J]. Th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1986,17( 2) : 31-40.
[20]Hines J M,Hungerford H R,Tomera A N. Analysis and synthesis of research on responsible environmental behavior: A meta-analysis[J].Th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1987,18( 2) : 1-8.
[21]Guagnano G A,Stern P C,Dietz T. Influences on Attitude-behaviorRelationships: A Natural Experiment with Curbside Recycling[J].Environment and Behavior,1995,27( 5) : 699-718.
[22]Dietz T,Stern P C,Guagnano G A. Social Structural and Social Psychological Bases of Environmental Concern[J].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1998,30( 4) : 450-471.
[23]Blake J. Overcoming the ‘Value-Action Gap' in Environmental Policy: Tensions between National Policy and Local Experience[J].Local Environment,1999,4( 3) : 257-278.
[24]张晓杰,靳慧蓉,娄成武.规范激活理论:公众环保行为的有效预测模型[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8(06):610-615.DOI:10.15936/j.cnki.1008-3758.2016.06.010.
[25] DUNLAP,RILEY E,KENT D,et al. Measuring Endorsement of the New Ecological Paradigm:A Revised NEP Scale[J].Social Issues,2000,(56).
[26]张晓杰,胡侠义,王智奇.价值—信念—规范理论:公众环保行为研究的新框架[J].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8(04):33-40.
[27]HUNGERFORD H R,VOLK T L.Changing Learner Behavior Through Environmental Education[J].Th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1990,21(3):8-21.
[28]彭远春.城市居民环境认知对环境行为的影响分析[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21(3):168-174.
[29]龚文娟,雷俊.中国城市居民环境关心及环境友好行为的性别差异[J].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3):340-345.
[30]钟念,李廉水,张三峰.公众环境关心与环境友好行为的非一致性研究: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分析[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20(3):49-56.
[31]洪大用,范叶超.公众环境知识测量:一个本土量表的提出与检验[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6,30(4):110-121.
2024年7月,河海大学“追光”支教实践调研团在安徽省涡阳县圣尧小学支教期间,发现当地存在水华、垃圾乱扔等环境污染问题。为促进我国推动绿色发展,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不仅需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还需要民众的广泛参与。
本文基于2024年涡阳县部分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调查数据,通过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对我国公众私人领域环境行为和公共领域环保监督参与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环境态度和环境知识水平均与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环境行为呈正相关关系,但对政府环保工作力度评价和环境状况感知等外部因素对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环境行为的影响存在差异。公众对中央政府环保工作力度的评价均与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环境行为呈正相关,但公众对所在地政府环保工作力度评价与通过媒体和体制化渠道进行环保监督的行为呈负相关;感知到的当地环境问题影响严重程度对于私人领域环境行为的影响更大,对周边污染企业感知对于公共监督参与行为的影响更大。此外,在社会人口特征方面,年龄与公私领域环境行为均呈正相关关系,但性别、受教育程度、居住地类型对公私领域环境行为的影响方向存在差异。
关键词:环境行为;影响因素;环保公众参与;环境保护
目录
摘 要
第1章 绪论
1.1研究背景
1.2研究意义
1.3概念阐述
1.3.1环境保护
1.3.2环境行为
1.3.3环境公众参与
第2章 文献综述
2.1文献回顾
2.1.1国内文献回顾
2.1.2国外文献回顾
2.2研究综述
第3章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3.1理论基础
3.1.1“规范-激活”理论
3.1.2“价值-信念-规范”理论
3.2研究假设
3.2.1个体心理因素
3.2.2外部因素
3.3.3社会人口特征因素
第4章 研究设计
4.1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4.2变量设计
4.2.1被解释变量
4.2.2解释变量
4.2.3控制变量
4.3模型构建
第5章 实证分析
5.1描述性统计
5.2多重共线性检验
5.3回归结果分析
5.3.1环境态度与环境行为
5.3.2环境知识与环境行为
5.2.3环境状况感知与环境行为
5.2.4政府环保工作与环境行为
5.2.5社会人口特征变量与环境行为
第6章 结论与建议
6.1实证研究结论
6.2研究建议
参考文献
第1章 绪论
1.1研究背景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加速,以及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环境问题逐渐显现,如空气污染、水体污染、土地退化、生物多样性的丧失等,这些问题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了严重威胁。因此,绿色发展理念应运而生,强调的是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保护环境,实现经济、社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此外,绿色发展还与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密切相关。联合国制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旨在到2030年解决全球的贫困、不平等、气候变化、环境退化等问题,其中就包括了绿色发展的理念。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绿色发展理念的研究和实施变得尤为重要,包括但不限于绿色能源、绿色建筑、绿色交通、绿色金融等方面的研究和实践,都是为了实现绿色发展的目标。在这样的背景下,河海大学“追光”支教实践调研团在安徽省亳州市涡阳县圣尧小学支教过程中发现,虽然当地生态环境在近年来得到改善,但是当地居民生态环境保护意识薄弱、并且缺乏相关环保知识,据此,“追光”支教团为传播生态环保知识设计了问卷并在当地展开调研。
1.2研究意义
生态环境保护关乎地球的生态平衡、人类的健康福祉以及可持续发展的未来。通过推广绿色生活方式和环保技术,我们能够减少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与污染,有效应对气候变化、空气污染、水资源短缺等全球性环境问题。生态环境保护的意义在于促进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和谐共生。它鼓励人们采用低碳、节能、可循环的生产和消费方式,不仅推动了绿色经济的崛起,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和经济增长点。同时,绿色环保行动也是提升公众环境意识、培养责任感的重要途径,促进了社会文明的进步,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1.3概念阐述
1.3.1环境保护
环境保护,指的是人类为解决现实或潜在的环境问题,协调人类与环境的关系,保障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而采取的各种行动的总称。其涵盖了众多方面,包括但不限于对自然环境(如大气、水、土壤、生物等)的保护,防止污染和破坏;对生态系统的维护,促进生态平衡;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以确保资源的可持续性;以及通过教育、法律、政策等手段,提高公众的环境意识和推动全社会共同参与环境保护行动。环境保护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创造一个清洁、健康、美丽且适宜人类居住和发展的环境。
1.3.2环境行为
环境行为是指个体或群体与周围环境相互作用的各种表现和活动。它包括人们在日常生活、工作、学习和休闲等各种情境中,对环境的感知、认知、态度和行动。比如个人选择绿色出行方式、节约能源、垃圾分类等,企业采取环保生产措施、减少污染物排放等,以及社区组织开展的环保活动等都属于环境行为。环境行为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个人的价值观、知识水平、经济状况、社会文化背景,以及环境政策、信息传播等外部因素。对环境行为的研究有助于深入了解人类活动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从而制定更有效的环境保护策略和促进可持续发展。
1.3.3环境公众参与
环境公众参与,指的是社会公众在环境保护领域中,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自愿、平等地参与环境决策、环境管理、环境监督以及环境教育等相关活动的过程。其核心在于保障公众对环境事务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使公众能够有效地介入环境保护工作,促进环境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和透明化。公众可以通过参与环保组织、社区活动、公众听证会、提供意见建议、监督企业环境行为等多种形式,为环境保护贡献力量。环境公众参与有助于增强公众的环境意识,推动环境保护工作的有效开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以及可持续发展。
第2章 文献综述
2.1文献回顾
2.1.1国内文献回顾
国内环境行为研究起步较晚。在早期研究中,不同学者对于环境行为阐释不同。有学者从社会学的角度阐释环境行为,认为“环境行为是与特定社会的各种因素相关,以一定的社会关系形式进行并且其结果不仅会对环境产生影响,而且会影响到其他的社会关系的一种社会行为”(崔凤、唐国建,2010)[1]。有学者立足西方环境行为理论,认为“环境行为是采取有助于改善、增进或维持环境品质的行动。在生活中身体力行,以达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目的”(孙岩,2006)[2]。也有学者从环境行为与环境意识关系的角度出发,将环境行为从环境意识中进行了剥离,使环境行为成为后来专门而深入的研究方向(王玲,2011)[3]。目前我国环境行为内涵主要概括为广义和狭义。广义的环境行为不仅包括保护行为,也包括破坏行为,狭义的环境行为主要指环境保护行为(王晓楠,2019)[4]。本文研究的环境行为从狭义出发,即“个体在日常生活中主动采取的、有助于环境状况改善与环境质量提升的行为”(彭远春,2011)[5]。
学界对环境行为影响因素的解释众多,主要包括个体心理因素、社会人口特征因素和外部因素(贾如、郭红燕、李晓,2020)[6]。个体心理因素方面,公众个体所拥有的环境知识、环境治理技能、环境治理资源和身体素质等条件在参与环境治理行为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刘静静,2023)[7]。数字素养(刘长进、王俊雅等,2023)[8]、个人导向心理所有权与集体导向心理所有权(张琳琳,2023)[9]、自然共情、敬畏、环境价值观(龙燕棱、周永红,2023)[10]等也会公民环境行为有显著促进作用。社会人口特征因素方面,社会网络和社会规范对个体环境行为具有直接影响,社会信任和社会规范对团体环境行为具有直接影响(杨金梅,2024)[11]。社会交往、社会信任也均在环境行为中发挥积极作用(张莉琴、方醒等,2024)[12]。也有学者在研究社会阶层对环境行为的影响中提出,社会阶层对个人亲环境行为的影响差异:来自中层家庭的个人的亲环境行为最强;社会阶层对女性亲环境行为的影响程度高于男性;社会阶层对农村居民亲环境行为的影响程度高于城镇居民(王敏、王峰,2023)[13]。外部因素中,有学者认为当前我国在环境治理方面存在公众参与路径较少、参与途径不畅通等问题,政府对公众这一主体在环境治理当中发挥的作用不够重视(张成博,2021)[14]。同时,时间能力认知、信息畅通程度、设施便利程度、政策补贴情况也能在农户参与环境整治中起到正向的影响作用(张海鹏,2024)[15]。
2.1.2国外文献回顾
国外关于环境行为的研究早于国内(吴桂英,2014)[16]。国外对环境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可以从心理性因素以及内外因素结合两个方面梳理 (彭远春,2013)[17]。侧重心理性影响因素的研究模式方面,诸多学者直接利用计划行为理论对环境行为进行了研究,其中有学者提出:单独对感知到的行为控制加以考察时,其对环境行为有着显著作用;但将其与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综合考察时,感知到的行为控制对环境行为的作用无足轻重(KAISER F G、GUTSCHER H,2003)[18]。也有学者探讨了环境素养模式中相应变量对负责任环境行为的贡献力。结果显示,环境敏感度、环境行为策略知识与技能、个体控制观、群体控制观、对待污染与技术的态度、心理性别角色等影响环境行为,其中环境敏感度、环境行为策略知识与技能对环境行为最具影响力(Sia A P、Hungerford H R、Tomera A N等,1986)[19]。在借鉴计划行为理论以及参照环境素养模式的基础上,有学者提出一个负责任的环境行为模式,即除环境议题知识、行为策略知识、行为技能、态度、控制观、个人责任感以及行为意向与负责任的环境行为有关外,还存在影响环境行为的情境因素,如经济条件、社会压力、从事环境行为的机会等(Hines J M、Hungerford H R、Tomera A N,1987)[20]。内外因素结合的综合性研究方面,有学者提出预测环境行为的A-B-C模型。该模型将内在心理过程与外在条件加以整合,认为环境行为(Behavior)是个体一般与具体的环境态度(Attitude) 和社会结构、社会制度与经济动力等外在条件(External Conditions) 共同作用的结果(Guagnano G A、Stern P C、Dietz T,1995)[21]。而有的学者对环境主义的探讨则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侧重探讨社会人口特征与环境主义的关系; 二是着重探讨价值观、信念、世界观以及其他社会心理变量与环境主义的关系(Dietz T、Stern P C、Guagnano G A,1998)[22]。但是,也有其他学者指绝大多数环境行为模式具有局限的原因在于,其对个体、社会以及制度约束缺乏考虑,且往往假定人是理性的,能系统获取和利用各种信息。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其认为环境关心与亲环境行为之间存在个性、责任与可行性三个方面的阻碍。同时,其进一步指出日常生活领域的环境行为与不同的情境有关,最为一般的是社会结构与文化背景,如工业化程度、富裕水平、社会分化与整合的形式等,进而对行动者的生活以及体验现实的方式产生影响(Blake J,1999)[23]。
2.2研究综述
总体而言,对于公民生态环境行为的影响因素,无论是定性研究还是定量研究,国内外学者都有不同的观点。但学术界普遍认为,个体因素、社会因素和外部因素都会对公民环境行为产生影响。国内外文献中针对个别影响因素的分析较多,但是对影响因素综合性、全面性的研究较少。
第3章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3.1理论基础
3.1.1“规范-激活”理论
“规范-激活”理论认为个体规范是影响利他行为最直接的因素, 而个体规范受结果意识和责任归属的影响。
“规范-激活”理论主要由三个变量构成,分别是结果意识(awareness of consequence)、责任归属(ascription of responsibility)、个体规范(personal norms)。
“结果意识”是指个体对因为未实行利他行为而给他人或者其他事物造成不良后果的意识。通常情况下,个体对于在一定情况产生不良后果的感知越强烈,道德义务感则越强,个体则越可能激活个体规范去实行相应的利他行为。
“责任归属”是指个体对于不良后果的责任感。个体对于结果的责任感越强,就越有利于实行与个体规范相符的行为。
“个体规范”是指个体在一定情况下实行具体行为的自我期望。个体规范是被内化的社会规范,是自我的道德义务感。违反个体规范时,个体会产生罪恶感、自尊的丢失或者自我否定;反之,遵守个体规范时,个体会产生自豪感以及自尊的提升。
“规范-激活”理论自提出30多年来,已经被广泛地应用于研究西方发达国家的亲社会行为包括环保行为,并且被证明了该理论具有良好的预测力和解释力(张晓杰、靳慧蓉、娄成武,2016)[24]。
3.1.2“价值-信念-规范”理论
“价值-信念-规范”理论在“规范-激活”理论的基础上增加了“价值”、“新环境范式”两个主要变量。
1.价值
不同的价值取向会直接影响主体与其价值取向一致的环境保护意愿。通常,价值取向被区分为以下三类:
(1)利己价值取向:社会行为主体在实行环保行为时,将试图最大化个体利益,并且往往追求最大化自身经济利益。
(2)利他价值取向:社会行为主体在实行环保行为时,将注意到其他人类群体的福利,努力最大化社会群体利益,然而但这类人常常忽视非人类物种的福祉。
(3)利生物圈价值取向:社会行为主体在实行环保行为时,将不仅考虑到人类群体的福利,同时也会关注非人类物种的利益
通常来说,主体的价值取向对其行为没有较强的直接影响,二者间的关系通常还由其他因素所介导。因此价值变量成为“价值-信念-规范”理论模型因果链中最基础的研究变量。
2.新环境范式
新环境范式非常强调环境因素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和制约,认为人类的行为已经对脆弱的生态环境造成持续的不良影响。Dunlap等人(2000)[25]认为,认同新环境范式的人越多,环境状况改善的前景就越有希望。
“价值-信念-规范”理论认为价值取向、新环境范式、结果意识、责任归属和个体规范五个变量构成密不可分的因果链。在该因果链模式下,公众环保行为由个体规范所激活,个体规范由个体对因为未实行利他行为而给他人或者其他事物造成不良后果的意识(即结果意识)和个体对于不良后果的责任感(即责任归属)所激发,结果意识和责任归属本身则受到个体的价值取向和环境关心影响。
“价值-信念-规范”理论是“规范-激活”理论在环保行为研究中的拓展,在公众环保行为研究方面比“规范-激活”理论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张晓杰、胡侠义、王智奇,2017)[26]
3.2研究假设
3.2.1个体心理因素
随着心理学行为理论的兴起,早期环境行为研究汲取了心理学中的计划行为理论、“规范-激活”理论以及“价值-信念-规范”理论等,从而构建了环境行为领域的“态度-行为”研究框架。该框架认为,在特定情境下,个体的环境行为主要由其行动意愿所决定。“价值-信念-规范”理论认为,个人具有与环境状况关联的价值观,当个人意识到不采取某种行动会对环境带来负面影响而危及自己的价值,同时为自己有能力采取行动去减免环境威胁时,则感觉到有义务采取对环境有利的行动,就可能采取环保行为。因此个人环境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价值观、环境观、对自身行为潜在环境危害的认识、对自身行为能够减少环境危害的信心,以及由此产生的环境责任感。
Hungerford(1990)[27]从环境教育学的角度拓展了“态度-行为”框架,提出“知识-态度-行为”理论,认为环境知识能够通过态度影响行为。大部分实证研究承认环境知识对环境行为的重要作用。彭远春(2015)[28]根据CGSS2003和CGSS2010调查数据对环境认知水平和环境行为进行了探讨,发现环保知识、公众对环境污染危害程度的环境风险认知和环境问题严重性认知均对环境行为有显著影响。
基于以上文献提出研究假设:
H1:环境态度与涡阳县公民私人领域环境行为呈正相关关系。
H2:环境态度与涡阳县公民公共领域环保监督参与行为呈正相关关系。
H3:环境知识水平与涡阳县公民私人领域环境行为呈正相关关系。
H4:环境知识水平与涡阳县公民公共领域环保监督参与行为呈正相关关系。
3.2.2外部因素
随着研究的深入,国内外研究者越来越关注到,环境污染状况、政府环境治理行为、社会规范、等外部因素对公民环境行为的影响。
在外部因素研究中,环境质量状况和政府环境治理水平被视为最重要的两个影响因素。“污染驱动假说”认为,如果周围污染问题变得严重,公众会为维护自身环境权益而改善环境行动。同时,由于我国政府在环境治理中占据主导地位,对生态环境状况有着重要影响,也对公众行为有着引导和示范作用,因此国内学者将政府环境治理情况也视为重要的外部影响因素。
基于以上文献提出研究假设:
H5:涡阳县公民对当地环境污染状况的感知与其私人领域环境行为呈正相关关系。
H6:涡阳县公民对居住地周边污染企业的感知与其公共领域环保监督参与行为呈正相关关系。
H7:涡阳县公民所在地政府环保工作水平与涡阳县公民私人领域环境行为呈正相关关系。
H8:涡阳县公民所在地政府环保工作水平与涡阳县公民公共领域环境行为呈正相关关系。
H9:中央政府环保工作水平与涡阳县公民私人领域环境行为呈
正相关关系。
H10:中央政府环保工作水平与涡阳县公民公共领域环境行为呈正相关关系。
3.3.3社会人口特征因素
研究表明,社会人口特征因素如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和居住地等也会对环保行为产生显著影响。在年龄方面,有国内研究显示,中青年、中年、中老年会在私人环境领域表现得更好。在受教育程度方面,多数研究者承认受教育程度对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环境行为的促进作用。在居住地方面,大部分研究表明,我国居民环境行为存在显著的城乡差距和社会阶层差异,城镇居民、社会阶层较高居民的环境关注度更高。
但现有研究关于性别和收入的影响仍存在争议。在性别方面,大部分研究认为女性比男性环境行为表现更好。我国学者龚文娟(2007)[29]通过对200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发现女性比男性更加倾向于采取私人领域的环境友好行为。但也有研究表明,性别假设不一定适用于所有环境行为领域,如由于家庭分工不同,男性可能更多地采取家庭资源回收行为,且由于传统上男性更多地参与社会事务和政治活动,所以可能比女性更多地参与公共环保事务。
在收入水平方面,有观点认为高收入群体一般对环境问题更为敏感,如钟念(2018)[30]等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0年数据发现,公众收入水平与其环境关心和环境友好行为呈显著正相关。但也有相反的观点认为,低收入群体由于生活环境状况较差,从而更加关注环境问题,而社会经济状况较好的公众则关注较少。也有其他研究表明,收入对环境行为的影响并不显著,高收入群体与低收入群体的环境行为差距不大,因此收入因素对于公众环境参与行为的影响有待进一步研究。
第4章 研究设计
4.1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样本选取旨在全面且准确地反映研究主题所涉及的对象。总体范围界定为安徽省亳州市涡阳县,选择该总体是因为其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依据年龄将总体分为不同层次,以确保样本在各个层次上的分布均衡。样本规模确定为224人,此规模基于预先设定的统计功效分析和研究资源的实际情况。数据来源主要包括一手的问卷调查和二手的官方统计数据。问卷调查于7月22日至7月26日期间在安徽省亳州市涡阳县双庙镇进行,共设计了19个问题,涵盖了环境污染的种类、环境污染是否得到改善、居民在改善环境行动中的参与度等方面。在问卷发放和回收过程中,严格遵循调查规范,有效回收率为98%。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了数据清洗,剔除了无效和缺失值,随后采用SPSS 27软件对经验数据进行处理分析。然而,由于时间和资源的限制,样本规模可能相对较小,可能无法完全涵盖总体的所有特征。在后续的分析和结论中,将充分考虑这些局限性。
4.2变量设计
4.2.1被解释变量
鉴于公众在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环境行为存在较大差异,本研究将“私人领域环境行为”和“公共领域环保监督参与行为”作为主要因变量,全面考察其影响因素并比较影响因素的异同。
为得到私人领域环境行为变量,首先将公众在10个方面的环境行表现得分(1~5分)经过同向化处理后进行加总平均,并为了方便与公众的监督参与行为变量进行对比,根据平均分是否在4分及以上处理为二分变量,其中4分及以上意味着公众整体上“总是”或“经常”践行各类环境行为。同时,为了弥补多数研究将私人领域环境行为作为单一整体变量进行研究、无法比较不同类型行为差异的问题,本文选取“随手关灯、及时关闭电器电源”等节电行为和“选购绿色产品和耐用品、不买一次性用品和过度包装商品”绿色消费行为作为私人领域具体环境行为的因变量,其中前者代表着减少生活成本的环境行为,而后者代表着可能提高消费支出的环境行为。
公共领域环保监督参与行为变量为二分变量,来自于本次受访者对过去三年中是否针对企业环境污染问题采取过行动的调查,采取行动的渠道包括“直接找企业协商”“向当地政府相关部门反映污染问题”“向当地街道、居委会或村委会反映情况”“通过上访向上级政府反映污染问题”“向媒体反映情况,引起舆论关注”“寻求民间环保团体的帮助”和“把事情直接曝光到网上”。同时,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受访者使用不同监督渠道的比例差异较大,在过去三年中采取过监督行动的人群中,使用地方体制化渠道的比例最高,“向当地街道、居委会或村委会反映情况”占37.5%,“向当地政府部门投诉举报”占25.8%;其次是媒体渠道,选择“向媒体反映情况,引起舆论关注”占17.9%。因此选取“是否通过媒体渠道监督参与”和“是否通过地方体制化渠道监督参与”作为公共领域具体监督参与行为的因变量。
表1 被解释变量相关变量测量
| 行为类型 | 行为领域 | 具体环境行为 |
| 私人领域环境行为 | 关注生态环境 | “您平时关注生态环境信息吗?” |
| 节约能源资源 | “您平时会注意随手关灯、及时关闭电器电源吗?”“您认为您在外出就餐时适度点餐或餐后打包方面做得怎么样?” | |
| 践行绿色消费 | “您认为您在绿色消费如选购绿色产品和耐用品,不买一次性用品和过度包装,商品等方面做得怎么样?” “您购物时会自带购物袋吗?” “您平时会改造利用交流捐赠或买卖闲置物品吗?” |
|
| 选择低碳出行 | “您平时以步行骑自行车或乘公共交通工具为主,要出行方式吗?” | |
| 分类投放垃圾 | “您认为您在垃圾分类方面做得怎么样?” | |
| 减少污染产生 | “您会在节假日期间燃放烟花爆竹吗?” | |
| 呵护自然健康 | “您认为您在拒绝购买、使用、食用珍稀野生动植物或其他制品方面做得怎么样?” | |
| 公共领域环境行为 | 参与监督举报 | “在过去的三年中,您针对企业的环境污染问题采取过哪些行动?” |
环境态度:包括私人领域环境行为重要性和公众监督参与行为重要性,其中私人领域环境行为重要性变量,由受访者对十类环境行为对于保护我国生态环境的重要程度打分(1~5分),再进行加总平均得到,公众监督参与行为重要性变量由受访者对六类环保监督参与行为对于促进企业环境保护的重要程度打分(1~5分),再进行加总平均得到。
环境知识:环境知识指公众对于环境问题、环境科学技术和环境治理的一般性认知状况(洪大用,范叶超,2016)[31]本研究中由4道环保知识判断题回答正确数量进行测量,题目涉及“公民十条发布情况”“露天烧烤会产生PM2.5”,“雾霾的产生与散煤燃烧是否有关”和“全国统一环保举报热线电话是12369”,基于样本量考虑,将回答“不知道”的纳入错误选项。
环境状况感知:由受访者对当地环境状况的评价得出,包含“是否认为居住地周边有污染企业”和“认为当地环境问题对自身影响程度”两个题项。环境状况感知变量受到宏观的地方环境质量影响,但又更为具体地反映了公众对居住地周边环境的不同感受。外在的地方环境质量只有被公众内化为对环境质量的认知,才会进一步影响环境行为,因此用公众的个体环境状况感知变量替代宏观的地区环境质量变量。
政府环保工作:考虑到中国政府在环境治理领域的突出影响,在模型中纳入“政府环保工作状况”变量,由“对所在地政府环保工作力度评价”和“对中央政府环保工作力度评价”两个题项进行测量,赋值分别为0~10分。
4.2.3控制变量
根据既有研究,选取性别、年龄、居住地、受教育程度、工作单位性质和家庭税后年收入作为控制变量。综上所述,本研究所使用的变量描述见表2。
表2 变量定义表
| 变量 | 赋值 | |
| 因变量 | 私人领域环境行为 | 1=“总是”或“经常”,0=“几乎不”“很少”或“有时” |
| 节电行为 | 1=“总是”或“经常”,0=“几乎不”“很少”或“有时” | |
| 绿色消费行为 | 1=“总是”或“经常”,0=“几乎不”“很少”或“有时” | |
| 公众领域监督参与行为 | 1=参加过,0=没有参加过 | |
| 通过媒体渠道监督 | 1=参加过,0=没有参加过 | |
| 通过地方体制化渠道监督 | 1=参加过,0=没有参加过 | |
| 控制变量 | 性别 | 1=男性,0=女性 |
| 年龄 | 1=25岁及以下,2=26~40岁,3=41~59岁,4=60岁及以上 | |
| 受教育程度 | 1=大专/本科及以上,0=其他 | |
| 居住地类型 | 1=城镇,0=农村 | |
| 工作单位类型 | 1=政府部门或事业单位,0=其他 | |
| 家庭收入水平 | 1=10万元及以上,0=其他 | |
| 环境态度 | 私人领域环境行为重要性 | 1~5分依次代表“不重要”“重要性较低”“重要性一般”“比较重要”“非常重要” |
| 环保监督参与行为重要性 | 1~5分依次代表“不重要”“重要性较低”“重要性一般”“比较重要”“非常重要” | |
| 环境知识 | 环境知识答题正确数量 | 0~4分 |
| 环境状况感知 | 是否认为居住地周边有污染企业 | 1=“有很多”或“有一些”,0=“没有”或“不清楚” |
| 认为当地环境问题对自身影响程度 | 1=几乎没影响,2=影响较小,3=影响一般,4=影响较大,5=影响非常大 | |
| 政府环保工作 | 对所在地政府环保工作力度评价 | 0~10分代表从“非常弱”到“非常强” |
| 对中央政府环保工作力度评价 | 0~10分代表从“非常弱”到“非常强” |
本文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将考虑环境态度、环境知识水平、环境状况感知等因素对公众私人领域环境行为的影响来分析十个研究假设。为验证
假设H1:环境态度与私人领域环境行为呈正相关关系。
假设H2:环境态度与公共领域环境行为呈正相关关系。
假设H3:环境知识与私人领域环境行为呈正相关关系。
假设H4:环境知识与公共领域环境行为呈正相关关系。
假设H5:当地环境污染状况感知与私人领域环境行为呈正相关关系。
假设H6:当地环境污染状况感知与公共领域环境行为呈正相关关系。
假设H7:所在地政府环保工作水平与私人领域环境行为呈正相关关系。
假设H8:所在地政府环保工作水平与公共领域环境行为呈正相关关系。
假设H9:中央政府环保工作水平与私人领域环境行为呈正相关关系。
假设H10:中央政府环保工作水平与公共领域环境行为呈正相关关系。
构建两个Logistic回归模型:
模型1:分析私人领域环境行为(Y1)
Logit(P(Y1=1))=β0+β1A+β2K+β3E+β4L+β5C+β6Age+β7G+β8Education+β9Residence
模型2:分析公共领域环境行为(Y2)
Logit(P(Y2=1))=β0+β1A+β2K+β3E+β4L+β5C+β6Age+β7G+β8Education+β9Residence
其中,β为回归系数,Y1为私人领域环境行为,Y2为公共领域环境行为,A为环境态度,K为环境知识,E为环境状况感知,L为地方政府环保工作评价,C为中央政府环保工作评价,Age为年龄,G为性别,Education为受教育程度,Residence为居住地类型。
通过回归分析得到每个自变量的回归系数(β),可以判断各因素对环境行为的影响方向和显著性。
第5章 实证分析
5.1描述性统计
私人领域环境行为均值为0.2795,标准差为0.449,表明公众的节电以及绿色消费行为在日常生活之中较少做到;公众领域监督参与行为均值为0.6343,标准差0.482,表明该地区公众有一定的监督意识,但参与程度高低不平。综合各项数据表明本研究有进行的意义与可能。
表3 公众环境行为变量描述性统计
| 变量 | 赋值 | 均值 | 标准差 | |
| 被解释变量 | 私人领域环境行为 | 1=“总是”或“经常”,0=“几乎不”“很少”或“有时” | 0.2795 | 0.449 |
| 节电行为 | 1=“总是”或“经常”,0=“几乎不”“很少”或“有时” | 0.8903 | 0.312 | |
| 绿色消费行为 | 1=“总是”或“经常”,0=“几乎不”“很少”或“有时” | 0.5433 | 0.498 | |
| 公众领域监督参与行为 | 1=参加过,0=没有参加过 | 0.6343 | 0.482 | |
| 通过媒体渠道监督 | 1=参加过,0=没有参加过 | 0.1829 | 0.387 | |
| 通过地方体制化渠道监督 | 1=参加过,0=没有参加过 | 0.4007 | 0.490 | |
| 控制变量 | 性别 | 1=男性,0=女性 | 0.6473 | 0.478 |
| 年龄 | 1=25岁及以下,2=26~40岁,3=41~59岁,4=60岁及以上 | 2.2677 | 0.731 | |
| 受教育程度 | 1=大专/本科及以上,0=其他 | 0.7613 | 0.426 | |
| 居住地类型 | 1=城镇,0=农村 | 0.8482 | 0.359 | |
| 工作单位类型 | 1=政府部门或事业单位,0=其他 | 0.2583 | 0.438 | |
| 家庭收入水平 | 1=10万元及以上,0=其他 | 0.4512 | 0.498 | |
| 环境态度 | 私人领域环境行为重要性 | 1~5分依次代表“不重要”“重要性较低”“重要性一般”“比较重要”“非常重要” | 4.3401 | 0.601 |
| 环保监督参与行为重要性 | 1~5分依次代表“不重要”“重要性较低”“重要性一般”“比较重要”“非常重要” | 3.6236 | 0.865 | |
| 环境知识 | 环境知识答题正确数量 | 0~4分 | 0.5908 | 0.230 |
| 环境状况感知 | 是否认为居住地周边有污染企业 | 1= “有很多”或“有一些”,0=“没有”或“不清楚” | 0.6055 | 0.489 |
| 认为当地环境问题对自身影响程度 | 1=几乎没影响,2=影响较小,3=影响一般,4=影响较大,5=影响非常大 | 4.1486 | 0.830 | |
| 政府环保工作 | 对所在地政府环保工作力度评价 | 0~10分代表从“非常弱”到“非常强” | 5.6200 | 2.528 |
| 对中央政府环保工作力度评价 | 0~10分代表从“非常弱”到“非常强” | 6.8600 | 2.290 |
5.2多重共线性检验
本研究运用SPSS27分析软件对公众私人领域环境行为和公共领域监督参与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在回归分析前,对模型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表明各模型的VIF值均大于1且小于3,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5.3回归结果分析
表4 公众环境行为相关变量回归分析结果
| 影响因素 | 私人领域环境行为 | 公共领域监督参与行为 | ||||
| 模型一:私人领域总体行为 | 模型二:节电行为 | 模型三:绿色消费行为 | 模型四:监督参与总体行为 | 模型五:通过媒体渠道监督 | 模型六:通过地方体制化渠道监督 | |
| B值 Exp(B) |
B值 Exp(B) |
B值 Exp(B) |
B值 Exp(B) |
B值 Exp(B) |
B值 Exp(B) |
|
| 性别 | -0.779∗∗∗ 0.459 |
-0.137∗∗ 0.872 |
-0.088∗∗ 0.915 |
0.050 1.051 |
0.608∗∗∗ 1.837 |
0.129∗∗∗ 1.137 |
| 年龄组(25岁及以下) | ||||||
| 26~40岁 | -0.020 0.981 |
-0.055 0.947 |
-0.177∗∗∗ 0.837 |
0.216∗∗∗ 1.241 |
0.199∗∗ 1.221 |
0.255∗∗∗ 1.290 |
| 41~59岁 | 0.533∗∗∗ 1.704 |
0.329∗∗∗ 1.390 |
0.220∗∗∗ 1.247 |
0.459∗∗∗ 1.582 |
0.270∗∗∗ 1.310 |
0.441∗∗∗ 1.554 |
| 60岁及以上 | 1.372∗∗∗ 3.942 |
0.786∗∗∗ 2.196 |
0.865∗∗∗ 2.374 |
0.539∗∗∗ 1.714 |
0.118 1.125 |
0.648∗∗∗ 1.912 |
| 受教育程度 | 0.308∗∗∗ 1.360 |
0.242∗∗∗ 1.274 |
0.362 1.436 |
-0.158∗∗∗ 0.854 |
0.232∗∗∗ 1.261 |
0.005 1.005 |
| 居住地类型 | 0.226∗∗∗ 1.254 |
-0.042 0.959 |
0.011 1.011 |
-0.127∗∗ 0.881 |
0.172∗∗ 1.187 |
-0.081 0.923 |
| 工作单位类型 | -0.021 0.980 |
-0.041 0.960 |
0.084∗ 1.088 |
0.058 1.060 |
-0.059 0.943 |
0.198∗∗∗ 1.218 |
| 家庭收入水平 | 0.004 1.004 |
-0.203∗∗∗ 0.816 |
0.118∗∗∗ 1.126 |
0.022 1.022 |
0.077 1.080 |
0.147∗∗∗ 1.159 |
| 环境态度 | 0.234∗∗∗ 1.263 |
0.092∗∗∗ 1.097 |
0.117∗∗∗ 1.125 |
0.325∗∗∗ 1.384 |
0.291∗∗∗ 1.338 |
0.290∗∗∗ 1.336 |
| 环境知识答题正确数量 | 0.989∗∗∗ 2.688 |
0.714∗∗∗ 2.043 |
0.900∗∗∗ 2.458 |
1.287∗∗∗ 3.624 |
1.062∗∗∗ 2.892 |
1.438∗∗∗ 4.213 |
| 是否认为居住地周边有污染企业 | -0.071 0.932 |
-0.022 0.978 |
0.095∗∗ 1.100 |
0.025 1.025 |
0.322∗∗∗ 1.380 |
0.358∗∗∗ 1.431 |
| 认为当地环境问题对自身影响程度 | 0.313∗∗∗ 1.368 |
0.126∗∗∗ 1.134 |
0.202∗∗∗ 1.223 |
0.028 1.028 |
0.216∗∗∗ 1.241 |
0.180∗∗∗ 1.197 |
| 对所在地政府环保工作评价 | 0.004 1.004 |
-0.050∗∗∗ 0.951 |
0.018∗ 1.018 |
0.007 1.007 |
-0.066∗∗∗ 0.936 |
-0.018∗ 0.982 |
| 对中央政府环保工作评价 | 0.095∗∗∗ 1.100 |
0.129∗∗∗ 1.138 |
0.065∗∗∗ 1.067 |
0.065∗∗∗ 1.067 |
0.042∗∗∗ 1.043 |
0.072∗∗∗ 1.075 |
| 常量 | -4.542∗∗∗ 0.011 |
0.240 1.271 |
-2.522∗∗∗ 0.080 |
-2.079∗∗∗ 0.125 |
-5.223∗∗∗ 0.005 |
-4.125∗∗∗ 0.016 |
| 卡方 | 489.669∗∗∗ | 140.285∗∗∗ | 369.456∗∗∗ | 635.018∗∗∗ | 410.611∗∗∗ | 774.736∗∗∗ |
5.3.1环境态度与环境行为
由回归分析结果可知,环境态度与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环境行为均成正相关关系。考虑到控制变量,公众认为私人领域环境行为对于保护我国生态环境的重要性每提高一个等级,其积极采取私人领域环境行为的概率比原来提升26%,积极节电和选购绿色产品的概率比原来分别提升10%和13%。同时,公众认为公共监督参与对于促进企业环境保护的重要性每提升一个等级,其针对企业环境污染问题采取过监督行为的概率比原来提升38%,通过媒体渠道和地方体制化渠道监督的概率均比原来提升34%。由此可以验证假设1和假设2,在“价值-信念-规范”理论的作用下,若公众认为自身的环境行为越重要,就会更加积极的采取行动。
5.3.2环境知识与环境行为
根据回归结果,环境知识水平与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环境行为均呈正相关关系,且对公共监督参与行为有较大影响。四道环境知识判断题中,公众每多答对一道题,则私人领域环境行为表现较好的可能性将是原来的2.69倍,“总是”或“经常”节电和选购绿色产品的可能性分别是原来的2.04倍和2.46倍,采取过监督参与行为的可能性将是原来的3.62倍,通过媒体渠道监督和通过地方体制化渠道监督的可能性分别是原来的2.89倍和4.21倍。综上,可以验证假设3和假设4,证明了环境知识对公、私领域环境行为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5.2.3环境状况感知与环境行为
模型一、二、三显示,环境状况感知对私人环境行为有显著影响。在控制变量的条件下系统地改变影响因素,受访者认为当地环境问题对其自身影响的严重程度与私人领域行为、节电行为和绿色消费行为均呈正相关关系。同时还认为当地环境问题的影响程度每严重一个单位,认为私人领域环境行为受影响的可能性比原来提升37%;主动节电的可能性较原来提升13%;积极进行绿色消费的可能性比原来提升22%。
由模型四、五、六可知,环境状况感知与监督参与总体行为无显著相关性,但对通过媒体渠道监督和通过地方体制化渠道监督均呈正相关关系。在控制变量的条件下,受访者认为居住地周边存在污染状况进尔通过媒体渠道监督的可能性提升38%,通过地方体制化渠道监督的可能性提升43%,说明受访者所代表的公众群体对居住地周边污染源反应程度较对私人领域环境行为污染的感知程度更强,同时采取措施维护自身权益的概率也更高。
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公众居住地附近污染源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一旦公众感知到生活环境周边存在污染状况,出于自身环境安全权益考虑,就会更迫切地想要通过专业的方式对污染源采取措施,同时自家附近的污染源相较于较远的污染源而言更可能激发公众监督参与的责任感和行动力。同时,公众认为当地环境问题的影响严重程度每上升一个单位,则通过媒体渠道监督和通过地方体制化渠道监督的概率比原来分别提升24%和20%。这基本验证了假设5和6的“环境污染驱动论”。
5.2.4政府环保工作与环境行为
公众对中央和所在地政府环保工作力度评价对其公共与私人领域环境行为均有显著影响,但在影响方向上有一定差异。对中央政府环保工作力度评价的影响程度相对较大。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公众对中央政府环保工作力度评价与公共和私人领域环境行为均呈正相关关系,且对节电行为、绿色消费行为、通过媒体渠道监督和通过地方体制化渠道监督均有一定正面影响。这可能是由于全国环保工作力度的加强对公众环保行为有潜移默化的表率作用,有助于提升公众的环境意识和责任感,从而积极践行各类环保行为。以上结果验证了假设7和假设8。但是,与假设九和假设十不相符合的是,公众对所在地政府环保工作力度评价对公共和私人领域总体环境行为均无显著影响,并且与通过媒体渠道和地方体制化渠道监督呈负相关关系,尤其是对通过媒体渠道监督的负向影响相对较大。这可能是因为地方政府环保工作力度与当地环境质量关系更密切,因此公众认为如果当地政府有能力保护好环境,就降低了监督参与的紧迫感,即便要监督参与,也更倾向于选择地方体制化渠道而不是媒体渠道;相反,如果公众认为所在地政府环境管理工作不利,那么公众将更加迫切地使用自身的监督权。
5.2.5社会人口特征变量与环境行为
社会人口特征变量中,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和居住地类型对公共与私人领域环境行为均有显著影响。
第一,性别对公共与私人领域环境行为的影响不同,女性更偏向于采取私人领域环境行为,而男性则更倾向于通过媒体渠道和体制化监督参与环保。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男性私人领域环境行为表现整体较好的概率仅为女性的二分之一不到,积极节电和选购绿色商品的概率也仅为女性的0.87倍和0.92倍,但男性通过媒体渠道和体制化监督的概率是女性的1.84倍和1.14倍。
第二,年龄与公共与私人领域环境行为均呈正相关,且年龄对私人领域环境行为影响较对公共领域环境影响大。40岁以上的群体更倾向于采取私人领域环境行为,而60岁及以上人群私人领域环境行为表现较好的概率是25岁及以下人群的近4倍,节电和绿色消费行为也呈现出一致的趋势。25岁以上人群在公共监督参与领域的表现均好于25岁及以下青年群体,60岁及以上人群总体监督参与行为表现相对最好,但相比私人领域环境行为增幅较小,且根据显著度和系数可知,年龄对通过体制化监督的正向作用比通过媒体渠道监督更大。
第三,受教育程度对公共与私人领域环境行为的影响不同。一方面,高学历人群的私人领域环境行为比低学历人群表现相对较好,在节约用电方面也更为积极;另一方面,高学历人群监督参与行为总体相对较少,但更多地通过媒体渠道监督,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高学历人群更善于使用媒体资源表达自身诉求。此外,受教育程度对公众购买绿色产品等色消费行为和通过体制化监督无显著影响。
此外,家庭年收入与私人领域环境行为总体不显著相关,但与节电行为和绿色消费行为均显著相关,且呈反向关系。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家庭年收入10万元及以上的家庭更倾向于随手关灯、及时关闭电器的概率是收入较低家庭的0.82倍,但在购买绿色产品和耐用品等绿色消费方面,能够做到的概率是收入较低家庭的1.13倍。这意味着,各类私人领域环境行为存在较强的异质性,在研究收入水平和便利性等因素时不能只考虑对总体环境水平的影响,还要考虑对不同类型行为的影响差异。
第6章 结论与建议
6.1实证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2024年涡阳县部分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调查数据,对我国公众私人领域环境行为和公共领域监督参与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对比研究,通过影响因素模型搭建与回归分析,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1)环境态度与环境知识与公私领域环境行为成正相关关系。环境态度会引导环境行为,而当大众的环境知识水平越高,公民更愿意采取环境友好行为。其主要机制是,大众通过环境知识的学习,把正确的环境态度和制度规范转变为自己的价值观,潜移默化于生活中,从而约束自己的行为。其中,环境知识水平对公共监督参与行为的影响相对较大。
(2)环境状况感知能够影响公私领域环境行为,但影响程度存在差异。环境状况感知中当地环境问题对私人领域环境行为存在显著影响;居住周边存在污染企业对其几乎没有影响。其中,对周边污染企业的感知对公共监督参与行为的影响更大,感知到周边存在污染企业,公众更愿意通过媒体渠道或地方体制化渠道采取监督行动。
(3)公众对中央和所在地政府环保工作力度评价对其环境行为的影响存在差异,公众对中央政府环保工作力度评价的影响相对较大,且呈正相关;对所在地政府环保工作力度评价与公私领域整体环境行为不显著相关。其中,经济奖励类政策对居民的环境行为影响显著,命令式对公众环境行为无明显影响。
(4)不同的公民禀赋对生态环境行为的影响存在差异。年龄对环境行为影响呈正相关关系。性别、受教育程度、居住地对公私环境行为影响差异化,女性更愿意主动以个人行为去保护生态环境,而男性更积极地参与环境法规与环境监督活动;高学历者相对于低学历人群存在更多的环境友好行为,且更多地进行环境法规的了解与环保状况的监督;城市居民较农村居民的私人领域环保行为表现较好,但总体上也缺乏对环保的监督活动。
(5)家庭收入水平对与具体的环境行为有一定影响,与降低生活成本的节电行为呈负相关,但与可能提高消费支出的绿色消费行为呈正相关。
6.2研究建议
根据此次调研实证研究得出的,对公私领域生态环保行为的积极正相关关系,本文得出以下启示:
(1)加强生态知识的宣传教育,提高公民的生态知识认知。借助电视、网络等传播媒介让生态意识深入人心,推动公民转变传统行为,引导树立以“生态利益”为中心的价值观。同时,可以进行社区环保大讲堂,科普系列活动,帮助培养公民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让居民自觉保护周边生活环境,将保护生态环境作为一种自觉的行为。
(2)有效化规范公民环保行为,多途径帮助环保政策落实落地。首先,要从多方面多种形式来推动居民知法、守法、用法,增强对环保法律制度的认识,使环保法制观念深入人心,进而增强公民的生态法制意识。但更要注意的是通过秸秆还田补贴、农业补贴、技术下乡等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举措对公民进行激励与引导。
(3)降低实施生态行为的障碍,提高公民对居住地附近环境状况感知和控制能力。要采取多种方式来减少居民在实施生态行为中所遇到的困难。首先,增加社会教育培训。如垃圾分类等。其次,增添多类垃圾桶、旧衣回收设施,绿色产品等环保基础设施和环保用品,为公民提供进行环保行为的多样化途径,方便进行生态友好行为。
参考文献
[1]崔凤, 唐国建. 环境社会学:关于环境行为的社会学阐释 [J]. 社会科学辑刊, 2010, 03): 45-50.
[2]孙岩. 居民环境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D], 2006.
[3]王玲. 国内环境行为研究综述 [J]. 农村经济与科技, 2011, 22(08): 15-7.
[4]王晓楠. 我国环境行为研究20年:历程与展望——基于CNKI期刊文献的可视化分析 [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19, 33(02): 22-31.
[5]彭远春. 试论我国公众环境行为及其培育 [J].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 11(05): 47-52.
[6]贾如, 郭红燕, 李晓. 我国公众环境行为影响因素实证研究——基于2019年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调查数据 [J]. 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2020, 45(01): 56-63.
[7]刘静静. 公众参与城市环境治理行为影响因素研究 [D], 2023.
[8]刘长进, 王俊雅, 李宁, 滕玉华. 数字素养对农村居民“公”领域亲环境行为的影响研究 [J].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3, 23(04): 12-20+83.
[9]张琳琳. “我的”还是“我们的”:心理所有权对亲环境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 [D], 2023.
[10]龙燕棱, 周永红. 自然共情与亲环境行为的关系:一个链式中介模型 [J]. 心理月刊, 2023, 18(20): 27-30.
[11]杨金梅. 社会资本对环境行为的影响机理研究 [J]. 当代经济管理, 2024, 46(08): 47-52.
[12]张莉琴, 方醒, 陈定倩. 社会交往对亲环境行为的影响:社会信任与环境关心的中介作用 [J]. 兵团教育学院学报, 2024, 34(04): 25-31.
[13]王敏, 王峰. 社会阶层、环保认知与亲环境行为——基于环境社会学视角的实证研究 [J]. 复旦公共行政评论, 2023, 02): 252-76.
[14]张成博. 基于TPB-VBN整合模型的公众参与环境治理行为影响因素研究 [D], 2021.
[15]张海鹏.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中农户参与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 [D], 2024.
[16]吴桂英. 国内环境行为研究综述 [J]. 经济研究导刊, 2014, 14): 7-9.
[17]彭远春.国外环境行为影响因素研究述评[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23(08):140-145.
[18]KAISER F G, GUTSCHER H. The Proposition of a General Version of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Predicting Ecological Behavior [J].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2003, 33(3): 586-603.
[19]Sia A P,Hungerford H R,Tomera A N,et al. Selected Predictors of Responsible Environmental Behavior: An Analysis[J]. Th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1986,17( 2) : 31-40.
[20]Hines J M,Hungerford H R,Tomera A N. Analysis and synthesis of research on responsible environmental behavior: A meta-analysis[J].Th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1987,18( 2) : 1-8.
[21]Guagnano G A,Stern P C,Dietz T. Influences on Attitude-behaviorRelationships: A Natural Experiment with Curbside Recycling[J].Environment and Behavior,1995,27( 5) : 699-718.
[22]Dietz T,Stern P C,Guagnano G A. Social Structural and Social Psychological Bases of Environmental Concern[J].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1998,30( 4) : 450-471.
[23]Blake J. Overcoming the ‘Value-Action Gap' in Environmental Policy: Tensions between National Policy and Local Experience[J].Local Environment,1999,4( 3) : 257-278.
[24]张晓杰,靳慧蓉,娄成武.规范激活理论:公众环保行为的有效预测模型[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8(06):610-615.DOI:10.15936/j.cnki.1008-3758.2016.06.010.
[25] DUNLAP,RILEY E,KENT D,et al. Measuring Endorsement of the New Ecological Paradigm:A Revised NEP Scale[J].Social Issues,2000,(56).
[26]张晓杰,胡侠义,王智奇.价值—信念—规范理论:公众环保行为研究的新框架[J].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8(04):33-40.
[27]HUNGERFORD H R,VOLK T L.Changing Learner Behavior Through Environmental Education[J].Th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1990,21(3):8-21.
[28]彭远春.城市居民环境认知对环境行为的影响分析[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21(3):168-174.
[29]龚文娟,雷俊.中国城市居民环境关心及环境友好行为的性别差异[J].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3):340-345.
[30]钟念,李廉水,张三峰.公众环境关心与环境友好行为的非一致性研究: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分析[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20(3):49-56.
[31]洪大用,范叶超.公众环境知识测量:一个本土量表的提出与检验[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6,30(4):110-121.
作者:杨昕怡、龚妍婷、杨罗绮、冯晓烜、邓佳妮、白雪娴、柳睿希、李科 来源:多彩大学生网
扫一扫 分享悦读
- 常州市红色文旅事业的潜力与挑战:深入调研报告
- 常州工学院理学院“赓续百年薪火,永承青春担当”通过暑期实践,深入常州红色文旅内地,潜心调研,挖掘潜力,寻找问题,推动常州红色旅
- 08-28
- 食品学子赴合肥社区委员会开展劳动协助活动
- 在2024年7月6日,暑期的炎炎烈日下。在往日冷冷清清的金湖社区委员会的门前迎来了一群充满磅礴生机于青春洋溢的实践团队,为其带来了热
- 08-28
- “筑梦非遗间,乡野绘新篇”实践队--非遗大观篇
- 山东大学管理学院“筑梦非遗间,乡野绘新篇”实践队走进济南非遗大观——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大观园进行实地调研
- 08-28
- 电亮黔程 | 双碳普及:践行绿色能源新,驱动低碳世界清
- 贵州铜仁德江县积极响应国家双碳政策,引进新能源产业,通过一系列创新和实践,为推动地方经济的绿色转型和可持续发展做出了显著贡献。
- 08-28
- “筑梦非遗间,乡野绘新篇”实践队--东阿阿胶篇
- 山东大学管理学院“筑梦非遗间,乡野绘新篇”实践队今天就走进非遗文化东阿阿胶的起源地——山东省聊城市东阿县进行实地调研
- 08-28
- 脐橙园中的岁月静好,奋斗路上的闪耀光芒
- 脐橙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在全球范围拥有巨大的市场。对于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的安远县,脐橙园在空间上表现出遍地“开花”的盛况。在
- 08-28
- 无锡学院学子三下乡:绿梦启航程,环保护家园
- 08-28
- “合”心兴乡路,“山”青智绘图——广财“百千万工程”突击队智援合山镇两村丰垌大迳记
- 阳光洒满阳江,青年乡土回甘。为响应广东省委关于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的重大部署
- 08-28
- 多彩大学生网©版权所有 客服QQ:471708534
-
大学生三下乡投稿平台